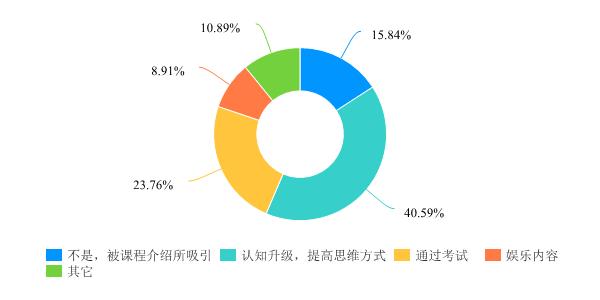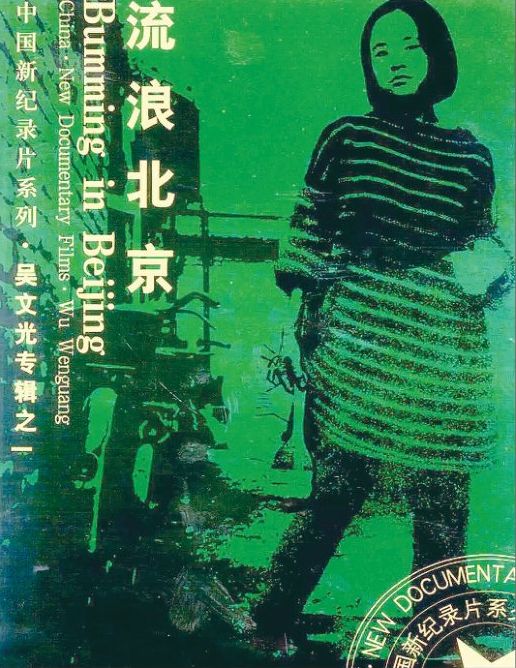
原创·首发·独家
一、从故事出发
《流浪北京》从结构上来看,可以分为六个部分,即:为什么来北京、住在北京、出国之路、留在北京的流浪者、张夏平的疯狂和《大神布朗》的登台。
在“为什么来北京”这部分里,牟森的话和高波的话让我印象深刻。牟森说过人只有三种选择:第一种,死,自杀;第二种,混,结婚生子对于他来说就是混;第三种,做自己选择的事情。对于牟森来说唯一的选择就是做自己选择的、自己喜欢的事情。可见牟森这样的艺术家认为,走结婚生子这样的路就是混日子,他们不愿意走普通人“循规蹈矩”的路,走这样的路对他们来说和死无异。我曾经听过一句话“只此一生,何必从众”,许多人都宣称自己要与众不同,但是真正做到的人却极少,大多数人都只是普通人中的一员,也许有过“仗剑走天涯”这样特立独行的想法,最后还是在柴米油盐中妥协了。牟森是真正践行了他的话的,他没有从众,他有“过柴米油盐日子无异于去 死”这样的决心,甚至在这几位“北漂艺术家”中,他也是冷静而坚定地在坚持梦想,其他人出国了,他也坚持留在北京继续做想做的事情。牟森在《流浪北京》中是顶着寸头,架着大框眼镜,穿着朴素气质沉稳地盘腿坐在出租屋地上的形象,他诉说着他希望有一个自己剧团的梦想。纵使他这时只是一个贫困的边缘人,他的剧团还是实验性质的,在当时看来他的话剧梦想几乎是难以实现的,但我相信大多数观众听见他诉说着自己的梦想,心里油然而发的是尊敬与崇拜,而不是嘲笑他的不自量力。牟森在坚持自己的梦想这条路上,是一个英雄,他说了许多别人也说过的话,但是做到了许多别人想做、羡慕、却又做不到的事。
高波谈到“北漂”的选择时说“人多少有点盲流性”,从我的理解来看,他是想说人们是不由自主地被推着往前走的,有的人挤作一团,有的人被挤到一边,高波就是被挤到一边的那些人中的一个,所以他说“我是没办法”,但是他也表示“我也喜欢”“我觉得挺好”,因为被推着走也是他自己的选择,他给自己赋予了“freelance”的身份与价值,他希望一直是一个自由摄影师。我觉得高波总结的这句话就是这些“北漂艺术家”的心声———做自己喜欢做的,这就是盲流。
在“住在北京”这部分里,我们看到了几位北漂艺术家的真实生活问题,生活不能只有诗和远方,完全不考虑柴米油盐也活不下去。对于他们来说,放弃原本安逸的生活来北京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物质层面的匮乏压根不算什么,他们的想法和我在《瓦力》这部电影中看到的经典台词一样———“我们想要生活,而不是生存”。过于理想主义是行不通的,先是生存,才能有生活,梦想也要落在实处,影像忠实地记录下了北漂艺术家们的生存状况,他们的居住条件可以看出是非常恶劣的———栖身于各种破落的房屋并且居无定所,张夏平住在电视台单身宿舍中,她坦言经常在住房上需要别人帮助,有时候因为自己“太个性”,被人不理解,不太舒服。而张慈租住在北京的胡同里,她的身上带着艺术家的忧郁气质,说出的话有“出口成章”的意味,当她提到自己的食堂和澡堂都是北大的时候忍不住落泪,她还说有外国人来看她住的胡同说“好”,她面对镜头哭着说“好个屁”。
在“出国之路”这部分中,张慈出国事件是一条主线,穿插了其他几位北漂艺术家对于出国的想法。可以看出,对于当时的年青人来说,美国是一个美好的幻想,去美国是一种奢望,但张慈在谈到“出国梦”时,又提到了她希望在美国有“固定的生活、固定的房子、固定的存款、固定的汽车”。张慈的理想化生活里也是有现实成分的,说明她在生活中也处于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中,既有着无忧无虑写作的理想,又在生活窘迫的现实中困顿。张夏平对张慈出国这件事的看法是“不太高兴”,她认为张慈的做法是“为了出国把婚姻出卖了”,谈到自己对“出国”的想法,她说:“在出国这件事上我很自信,我肯定是能出国的,但是不是因为我想出国才出,我认为生命进程必然有这么一天。”从这里可以看出,张夏平的身上有艺术家那种骄傲甚至是自负,她是不甘平凡的人。
在“张夏平的疯狂”这部分中,着重展现了张夏平为艺术痴狂的状态,张在画廊里面癫狂地说:“不是我的声音,是上帝在说话,我他 妈的这世界就缺把火,烧起来”,她躺在画上喃喃自语:“上帝啊上帝啊你听见了吗?我他 妈的我是谁啊?太可怕了,我他 妈的什么人?我他 妈的不知道。”这个画面极其具有冲击性,我相信看见的人没有一个不会被触动,我看见张夏平的样子,第一反应是恐惧,而后又觉得敬佩,就像牟森的评价“艺术上应该达到那种纯粹状态,最好的艺术状态就是疯了之后。”这些不顾一切来到北京的艺术家是真正燃烧生命来追求艺术理想的人,他们的执着令我动容。
在“《大神布朗》的登台”这一部分里,戏剧参与人员的那封信里的话写出了这一代话剧人的真实想法:“产生幸福的要哭的感觉,共同的精神把这些人凝聚在一起,特别有力量温暖,戏剧说到底就是一群人聚在一起,他们之间有某种东西又把这种东西传递给别人。”从片中放出的《大神布朗》的演出片段可以看出,当时的话剧人是真正纯粹地在演出,他们的动作神态都显得专心而投入,表演者沉浸在角色情境中,甚至和角色“融为一体”,正如牟森所说,他们真正做到了“艺术就是生活本身,像苦行僧似的毫无保留的献身,生命力得到最完美的满足和宣泄”。
二、从视听表现出发———纪实美学的体现
吴文光在拍摄《流浪北京》时,最大程度地减少了人为修饰的痕迹,摄影机就像一个冰冷的物体,只存在着事实的记录者。这与安德烈·巴赞的纪实美学观念不谋而合,巴赞在文章《摄影影象的本体论》中提出“外部世界的影像第一次按照严格的决定论自动生成,不用人加以干预,参与创造。”《流浪北京》中大量使用长镜头来记录几位北漂艺术家的手法恰恰是这一理念的体现。
拍摄人物采访时,往往采用固定长镜头,导演的距离把握得刚刚好,透露出一丝疏离,却又完美地走近了几个主要人物,拍摄的视角和人物平行,人物不在画面的中心,被采访者在这样的镜头下无所遁形,却也极其自由,他们拥有无所顾忌地表现与表达自我的机会,直视着镜头与不知名的观众抒发自己内心的痛楚与遥远的梦想,他们没有一丝的虚伪与造作,在这样的画面里,我们看见的是一群纯粹的热爱艺术的人。采用固定机位来拍摄,关注人的同时也关注了人所处的环境,这部影片没有像其他的采访一样特意选取一个明亮舒适的采访地点,而是将机位直接架在这些艺术家的家里或是门口,在他们日常所处的地方,人与环境都做到了真实地展现,张夏平居住空间的逼仄昏暗、高波居住环境的陈旧杂乱、张慈居住环境的陈旧破落……无一不被摄影机忠实地记录了下来。
展现人物的生活状态时,也多次采用了长镜头的手法,如展现《大神布朗》的话剧排练,摄影机直接融入到这场戏中,在演员间穿梭,捕捉演员表演的情态,观众不自觉地就沉浸到这部话剧中,思考起话剧展现的故事。在展现张夏平开展前发疯的情态时,也用了长镜头来展现,对于我来说,这一段是全片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段,张夏平在发着疯,摄影机只是静静地观察,没有去打扰她的发疯,也没有受到她的影响,只是忠实地记录着她的癫狂,就像是真正的人的眼睛一样,还是一个极为理智冷静的人,能够关注到她的动作情态,却又不被她牵动太多的情绪。
影片全程运用同期声,加上极为克制地使用字幕的表现方式,让它显得更加的朴素、真实、可信。人物对着镜头将自己的故事娓娓道来,说到伤心时落泪,说到开心时微笑,迷茫时愣神,激动时手舞足蹈……喜怒哀乐的情绪,酸甜苦辣的生活,人生百态,尽数呈现。“还原生活的本来面目”本来就是一种高明的手法,同样的场景,类似于“张夏平发疯”,如果加上字幕和解说词,完全不会有这样的冲击力。吴文光这样简单的拍摄手法,也让影片有了“留白”的意味,与东方美学的气质符合,张夏平在采访中说“她最无助的时候,就去景山公园的望风亭,看黄昏中故宫的燕子归窝,内心会获得些许的安慰。”这时候观众的脑海里就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心绪不宁,渴望着远方的事物”的惆怅艺术家的轮廓,如果运用蒙太奇可以展现这一画面,这种美感反而会被大大削弱。最后,《流浪北京》这部影片做到了仅仅是事实呈现,而不是妄加评判,它没有刻意地植入导演的思维,这使影片呈现的画面更加具有感染力。